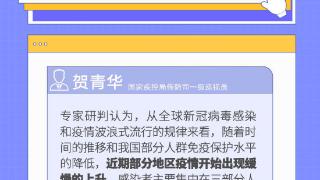栗树满山坡
本文转自:西安日报
□王璐
地处秦岭南坡的商洛,山地广阔,沟壑纵横,气候适中,不仅是人与动物栖息生存的福地,也是以落叶乔木为主的众多树木的故乡。即便在草木葱茏的春夏,依然要比南方的树木粗犷。
栗子树,就是其中的一种。栗子,是当地人对毛栗和板栗的统称。自312国道向南两公里,就是老家化庙老朋沟,面积不大亦不小,自古遍生野毛栗。相对于板栗,树型高大挺直,栗果却多比雀儿蛋还小。记得最早沟里果实硕大的板栗,也就三五十棵的样子吧,且多为面目沧桑的老树。
三十多年前,身兼生产队长的父亲,率领众乡亲开荒种田、解决口粮问题,连年春季还从外地运回优质种条,把遍山的野毛栗一棵棵嫁接为板栗,发展农村经济。沟里的板栗,于是很早就几乎已与野毛栗平分秋色了。我家板栗产量最多时,一年可达三四千斤,需要雇请两三个帮手连打带拾,好几天才能弄回家。一背篓一背篓的栗刺包儿倒在院落里,堆得像小山一样,盖上蒿草烂席捂几个昼夜,就接二连三地炸裂,露出暗红的栗果儿,再用剪子夹出,轻而易举。包儿大的,内有三粒甚至四粒,小的则仅有圆形的一粒。
打栗子,可是个苦差事,还得冒不小的风险。栗子成熟时,正是马蜂猖狂时节。顶着酷暑上山,随时还得防马蜂伤人事件发生。跟刺猬一般的栗刺包,对人的威胁同样不小。有一年,父亲正扬头把手中的竹竿甩得像蛇一样在树梢乱串,突然有一只竟正中他的左眼。一阵剧痛之后,他慢慢去摸时手掌血红一片……去医院后,万幸没伤及瞳孔,取出两根刺,不久即慢慢恢复。至于手臂扎刺,那是常有的事,无非事后用针挑挑;那点疼,对于下苦人不算疼。
行情好时,不等完全从刺包儿剥出,就有人上门收购。而行情差时,只得肩挑背驮,或用人力车拉着到当地集市上去卖。二、五、八逢集之日,我和父亲曾去七八里外的铁峪铺集镇,卖过多少回已记不清。一集没卖掉,等到下一集再拿出时,蛇皮袋里就有不少肉乎乎的白虫爬出。虫蛀的栗子,不得不贱价处理。
如何更好地储藏板栗?依据经验,探索出沙窝掩埋、塑料袋封装等多种办法。奇怪的是,有一年因干旱等气候原因,产量过低,板栗一下就成为抢手货,价格自不必说。而风调雨顺盛产之年,价格多半很低。农产品能否卖上好价钱,不仅取决于市场,有时还得靠运气。倒是那些机灵的商贩,往往赚得盆满钵满。板栗个大、漂亮,有的十几粒就是一斤。若论味道,真远不如毛栗好。在集市上买栗子,若是自己食用、不图好看,内行人宁愿买个小的野生毛栗,也不为板栗所动。
据说,栗子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生吃,也可熟吃,只是生吃不利于消化。上小学时,早晚都觉得肚里空空如也,栗子成熟的季节,大家上学多少都顺手揣一些当零食。有时正上课或自习,忽然有人放出闷雷般的屁来。大家明知是谁,爱出风头的人偏要不管不顾地咋呼几句:“站出来——是谁?”引发一阵哄堂大笑。
栗子还是以熟吃为主,最简便的吃法,不外乎是炒,陕南向来就有八月十五炒栗子的习俗。月圆如镜的夜晚,透过白窗纸的月光,一泻千里。围在锅台前的母亲,一边忙着揉面烙出香甜的月饼,一边把栗子倒在铁锅里炒,如燃放爆竹,啪啪作响……这样的场景,电影般无数次在我的脑海里回放。
有一道南北有名的美食——板栗烧鸡,吃来别具风味。用晒干或冰箱取出的板栗,剥皮下火锅,同样美味至极。我所生活的小城丹凤,县城广场附近有家以板栗磨粉为主加工的糕点——板栗酥,尤其在中秋期间,生意异常火爆,往往需排队很久才能买到。镇安的糖炒板栗,更是炒出一道陕西绝活,成为秦岭内外城市街头独特诱人的风景。
父亲去世六七年来,房前屋后成片的板栗树,全被荒草围困和淹没,大多奄奄一息,几乎没有几棵结果的了。零零散散,不便去打;打下,也滚进了草丛,找不出多少。为此老远驱车赶回,显然也很不合算,便连着几年都没再去管。每年不等成熟,就被蜂拥而至的乡邻们哄抢一空。既然自己无力采收,为什么又不允许别人捡拾呢?这样,总比糟蹋了好得多。
世之万物,本不分你我。在分享收获的喜悦、品尝大山馈赠的美味时,想必他们一定还能记起我的父亲。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明珠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