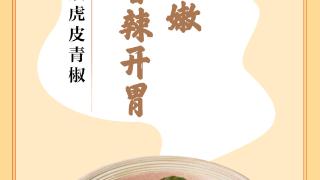匍匐在那片黄土地
本文转自:凉山日报
□浦站先
我们村有一片土地,是最为集中的,就像兄弟姊妹一样聚在一起。坎上是大哥的,坎下是二哥的,远一点是三哥的,再远一点是小弟的……一直连成一片,连成了村庄的希望。
那片土地黄得有些出奇,与我们常见的不太一样,黄土染在衣服上就像是染料一般,它又像极了“黄金”沙漠,细细的、柔柔的沙砾。不同于沙漠的是,那片土地生机勃勃,且能与其他土地一样保持潮湿。
我喜欢去那片黄土地,喜欢骑着我家那匹花白马儿去,让黄土把自己变成黄泥人。
布谷鸟在寂静的山林里歌唱,杜鹃花也在寂静的山林里“歌唱”,人们也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我们村的生活方式,我们没有吃早饭的习惯,当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刚照到村子时,也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吃完饭装上水,或装些干粮,或装些土豆,上了山,进了地,便是一天的劳动,晚上七八点钟吃晚饭,一天两顿一直如此。
我骑着花马,赶着黄牛,父亲背着犁头,我们向那一片能长出“金子”的地方走去。哦,对了,我们叫它:小平地。可能是因为它是众多山地比较成片的平地,故而这么叫着。
到了属于我家的那块地,看着诱人,像是里面埋着祖辈留下的宝藏。父亲将犁头放到地边,插进泥土。我把花马拴在有草的地方,然后将一根长长的藤条,落到老黄牛的背上,它惊了一下,可能皮厚,或是我的力气太小,没有感觉。我再使劲一抽,它出着大气,似乎有些恨意,但依旧奔向父亲的方向,这时它比我还要明白,得干活了,这是它的工作,早些干完就能早些放松。
父亲打小就是庄稼汉,对于套牛、犁地,那是再娴熟不过了。架好牛以后,父亲让我牵着老牛把第一环走出来,因为第一环在茫茫大地没有任何印记,老黄牛也就没有了方向。第一环走完了,它就能“老牛识途”了,一环又一环在父亲那悠扬的“着……着……着,咯咯咯……”的驾驭声中呈现,翻出来的黄泥土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闪着亮光。父亲看着老黄牛上道了,便吩咐我玩一会儿要记得给马儿换个有草的位置,我记下了,这是我的工作。
我撒腿跑向其他孩子所在的乐园,其实也就是几个兄弟姐妹。乐园,在那片土地上有三处,一处是地里,一处是野生桃林,一处是几棵大核桃树。我们在桃树和核桃树上把自己玩成了猴,无论粗枝还是细枝都能够来去自如。桃子熟了,我们乐不思蜀,品尝着野生桃的香甜。核桃熟了,我们的手被弄得漆黑,嘴弄得漆黑,桃仁儿都下了肚。我们还在树下“过家家”,用黄泥修房子,用黄泥做灶台,总之把黄泥拿来做成各种有趣的物品。到了午后,几个小孩就把各家带的土豆或什么的聚在一起,捡来柴火烧,其中一家的大人负责烧。烧熟以后,不论远近,小孩各自扯着嗓子喊各自的父母来吃晌午。
父亲把犁头深深地插在土里,然后端一些事先准备好的苞谷或草料放在牛的前面,它吃了起来。我们也开始吃了起来。我喜欢边吃边看老黄牛吃东西,总觉得它有好多的心事,和我一样多。它的眼神那么深邃,映进了高山、蓝天、黄土、森林……先是大口大口地将食物吞进肚子,我一直没想明白它的肚子看似那么小怎么能装那么多东西,更不明白它为什么能把细料和粗料分开。吞下去以后,才又站着慢慢悠悠地回嚼起来。它先从肚子里回一口食物到嘴里。若认真观察会发现很是奇妙,它吞下一口后提一口气“咕噜”一下,一坨食物就顺着食道爬了上来,跟我们装香肠差不多,往前推送到嘴里。食物到了嘴里,它开始咀嚼,不温不火。
吃过晌午,水壶里的水已差不多见底了。大人们又各自回到地里去劳动,我们小孩子便去取山泉水。
泉眼也在这片黄土地上,离我们种的地不足一公里。我们一人提着一只水壶,从树林里往下冲。还别说,多次把野兔从草丛里吓得魂不守舍。我们蹦跳着,打闹着,没有一丝的烦忧,这也许就是最美的童年。
取山泉水的地方,泉眼只有手指头那么大,但四季都不会断水。泉眼外是我们抠出来的如洗脸盆那么大的小水塘,再下面是得了这泉水馈赠的湿地。那里没有鱼、没有虾,唯独有的就是小螃蟹。
取水很慢,取完一壶要等上一会儿。我们就在湿地里玩水,找螃蟹。这里的螃蟹可不好找,四下都是石头缝,有时候看见一个洞,使出浑身解数把石头弄开,没准也是一场空。若是抓到一只螃蟹,几个孩子会高兴半天,这就是童年最简单的快乐。每次螃蟹没抓到几只,但乐趣满满,提着水壶回到了各自的地里,大人们抬起水壶“咕咚、咕咚”喝了个够。直到再次水壶见底,一天的劳作也就结束了。
夕阳打在那片黄土地上,金黄金黄的,大人们露着满意的笑容。大人们卸下一天的疲惫,赶着老黄牛,消失在暮色里。我也骑着陪伴我整个童年的花马消失在暮色里,再没像父亲一样把犁头深深插在那片黄土地里。
无论春夏秋冬,那片黄土地永不改色。
小平地,是父辈生活的希望,是哺育我们的“良田”。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用青春浇灌着那片黄土地,他们和它有着很深的情感,是我不懂的。他们把年华铺在了那山里,他们在那黄土地里匍匐前进。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明珠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