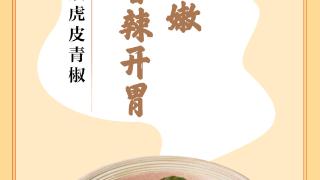又闻槐花香
本文转自:保定日报
□高国才
轻轻推开阳台的玻璃窗,一阵浓郁的芳香扑面而来。花香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楼下的槐花开了,一团团一簇簇挂在枝头真是繁花簇锦呢。映入眼帘的槐花让我的思绪飘远,不由得想起童年的许多趣事儿来。
那时,每到这个时节我就会和小伙伴相约背着小筐儿到村子东面的树林里去采槐花。在采之前我和小伙伴们都会根据各自的经验占据有利地形——挑一棵老槐树爬上去采摘。并不是老槐树上的槐花就好,而是它上面的刺针要比小树上少许多。我们爬到树上,骑在枝杈上面,扯过一根贴近自己的枝桠,采下一大把芳香四溢的槐花直接塞到嘴里大快朵颐。香甜的花汁溢出了嘴巴挂满了嘴角,那叫一个美啊!
吃够了,玩够了,闹够了,便开始大量的采摘,一直到小筐装得满满的。小伙伴们在嬉笑打闹中满载而归。
那时候刚承包责任田,每家的粮食还有些紧张。我们家弟兄四个都是半大小伙了,粮食总是在母亲精打细算中告罄。母亲虽是个农家妇女没有多少文化,却是个过日子的能匠巧手。为了丰富我们的饭碗菜盘子,总是找恰当的时间,把家里的孩子们动员起来,去村子旁边的树林子里撸槐花。
等我们把槐花采回来,母亲会洗干净沥去水分,再把槐花放在簸箕里滚上玉米面放在灶锅里蒸熟。在老家冀中一带这种食品叫“苦累”,也有叫麦饭的。至于为什么叫“苦累”,我是无从得知的。依我个人的理解应该是只有受苦受累的穷人家才会食用吧。
那时候,每家灶屋里都有一口大锅,足有一米见方。要蒸“苦累”了,锅里倒满水,上面铺上篦子、屉布,把拌好玉米面儿的槐花儿平铺在笼屉上。开始上锅蒸时,在灶头点燃从打麦场抱回家的麦秸,不急不慌等着锅里的水烧沸腾。
这时候,妈妈会招呼我去墙角摘几头蒜剥好,再捣成蒜末,用井水调成糊状的小料儿,点几滴香油。从田里耕作回来的父亲,顺便拔点地头上种的绿油油的春葱择洗干净。
蒸好嘞!出锅咯!阵阵香味儿弥漫在农家小院里,谁从家门口经过都会驻足招呼一声:你家又做槐花“苦累”啦?!还眼巴巴看着主人家,仿佛你一礼让他就会见坡下驴进屋吃上一大碗。
母亲给我们每个人拿蓝边大碗盛上半碗“苦累”,调上蒜泥拌的小料,撒上一把碧绿的小春葱,经典美食“苦累”就在眼前了!金黄的玉米面、洁白的槐花、碧绿的小春葱伴着蒜泥的辛辣,刺激着你的味蕾,保准让你食欲大开。坐在自己家的小院子里,听着收音机传来河北梆子高亢有力的唱腔,那叫一个美!
有时槐花采得多了,把吃剩的槐花拿来喂猪也是一种再利用。据说槐花虽好却不能多吃,吃多了会引起下肢浮肿。我们这年龄是没有见过的,估计是更艰苦的年代,老一辈们肚里没有粮食,全是吃这些槐花造成的吧。
今天再回家乡,村东的那片树林已被人们垦荒种上经济作物,一棵槐树也不见了。院子里的槐树也因为家里翻盖楼房嫌弃遮挡采光被伐去了。妈妈年至耄耋,步履蹒跚,再也不能为我们做“苦累”那么好的美味了,但槐花儿那种浓浓的香味儿时常飘荡在记忆里。
那是家的味道!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明珠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